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啥米? - 廖福特研究員談人權研究、公共參與及學術生涯(下篇)

採訪、撰稿:楊雅雯(中研院法律所博士後研究員)
攝影:汪正翔
上篇請見此連結(另開新視窗)
問:老師現在的研究重心,好像移到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上的權利。經濟社會權利通常會涉及資源分配,您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如何去落實這種更難落實的權利呢?
廖:這就是我剛才說的,涉及制度與系統性規劃的問題,這種議題在個案中不易解釋清楚。例如南鐵東移涉及居住正義,有二戶爭執到最後,但其他人都已拆除,大家又會說那個案子涉及每年有多少人要通行,孰是孰非說不清。
以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角度來講,就會需要全面性地瞭解各種可能性,委員背後也需要系統性的資源,許多不同背景的人員支持委員職權的行使。
問:所以老師認為國家人權委員會就是提出系統性資源,來面對人權問題的機制?
廖:對,重點在於國家人權委員會和行政權的角度不同。行政權的資源絕對比其他機關都大,國家人權委員會相對下資源還是有限,但它是以人權的角度出發。在南鐵東移案中,台南市長與行政院想的是交通建設的問題,可是人權委員看的是人權角度,從徵收、拆遷措施所涉及的居住正義議題,提供人權上不同角度的意見,也不同於人權團體專注在團體核心議題的角度。國家的人權委員會,仍是國家的,它要善用國家所給的資源從人權去思考。國家人權委員可能因而會處在一個困難的位置,無論是民間或政府都予以批評,但它核心的就是要善用國家資源從人權角度為國家做系統規劃,這才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所需扮演的角色。
問:幾年前我曾與萍水相逢的機上旅客聊到臺灣的人權進展,我的觀察是婚姻平權可能有助於外交,他則感到頗為質疑,質問外國人為什麼要關心我們的人權?這反映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他的生活經驗是外交領域講什麼人權?弱國就是無外交。臺灣好像只是地球上無足輕重的孤島,對他來說,談人權進展可以促進外交簡直天方夜譚。對於這樣想法的人,以老師之前的經驗,會想要告訴他什麼?
廖:首先,我們應該重新去理解人權外交。過去聽到的「人權外交」,都是強大的國家以人權之名,要求與它交往互動的國家,必須提升人權狀況,不然就取消經濟優惠或施加制裁,無論來自美國或歐盟,過去我們聽到的人權外交是這個模式,我們這個小國怎麼可能去扮演這個角色?
但現在人權外交是指,臺灣人權狀況變好後,可以與其他一樣著重人權的國家有更好的互動基礎,是一個伙伴結盟關係,因為我們理念相同、對人權概念的著重相同、有相同的實踐。如同英諺所說,相同羽毛的鳥會聚在一起。因為共同的信念而聚集,彼此互動更緊密,這個互動關係就叫外交關係。
所以有沒有邦交與人權外交是沒有關係的,重點在雙方或多方對人權議題是否著重,我們的人權外交與其他強國的國家人權外交,面向是完全相反的,其他國家是針對人權狀況不好的國家,對我們來說重點則是重視人權帶來更多的聯繫。
所以臺灣任何人權的改善,都可以稱為是人權外交的基礎。同婚很顯然會是例子。在國內讓同志婚姻合法化後,很多有同婚的國家會覺得你跟我一樣。還有另一面是非政府層級的外交、民間團體的互動,同婚合法化後有很多同婚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的民間團體很羨慕臺灣,這時臺灣是別人瞭解與互動的對象。這對臺灣是很可行的。
不過我要強調,人權外交是副產品,是附隨效應,主產品還是在人權本身。我們主要的目標還是要放在幫助臺灣建構更好的環境、更好的成果。人權改善不是為了外交,而是人權改善以後很自然地形成了後續的副產品,這才是人權外交合理的討論脈絡,不能為了外交而人權,而是人權好而延續了外交的改善。有時候為了促使政府有動力去改善人權,會拿外交作為理由,這是民間團體在推動的時候的策略之一,有些策略是攻擊、批評,有些策略則是誘使。但我們知道那就是策略,還是要瞭解最主要的訴求是人權的改善,對外交有幫助是附隨的,千萬不要本末倒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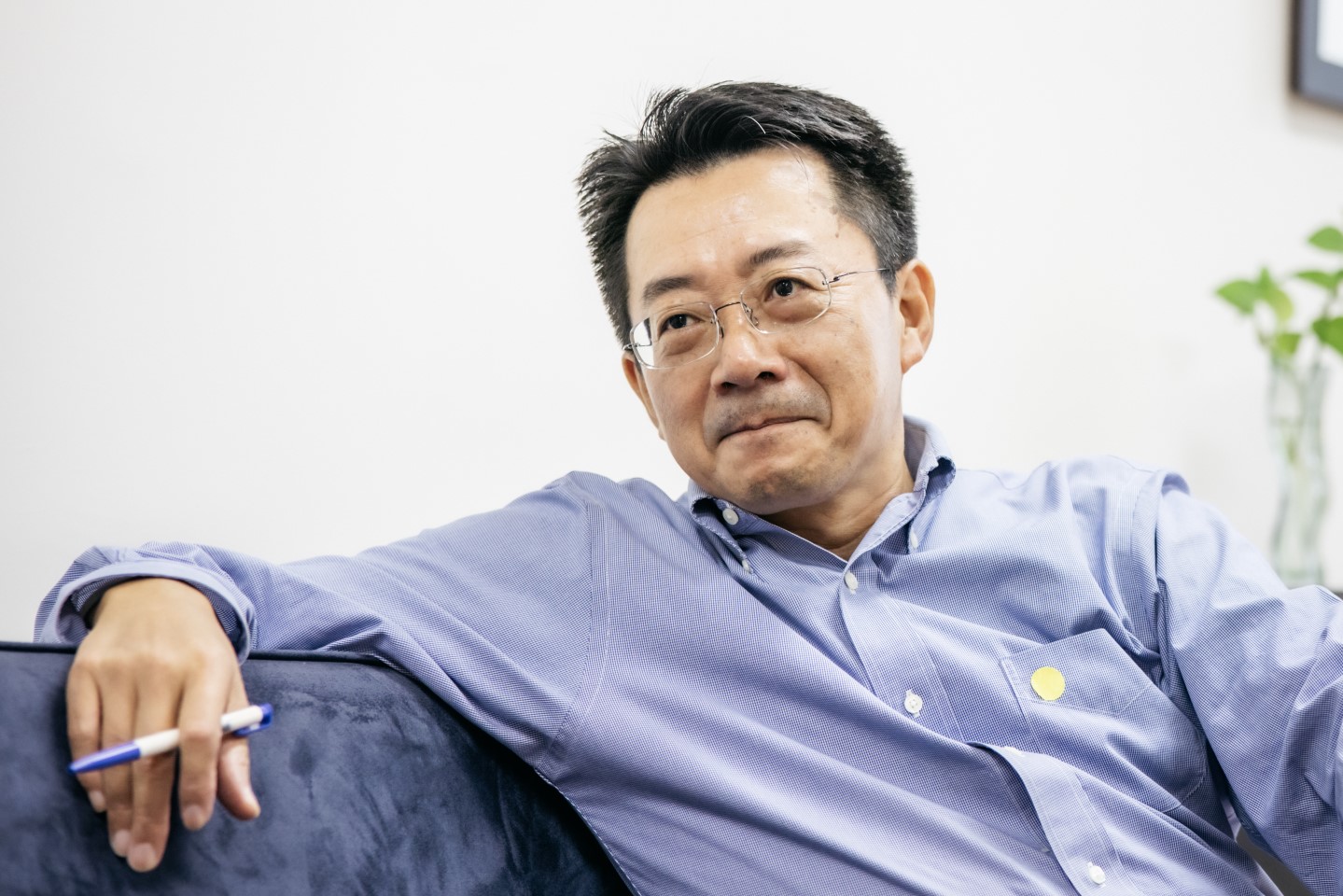
問:老師提到過去二十幾年都在角色三合一,學術工作、民間團體、政府諮詢。但可能有些人覺得學術工作跟實務之間,要維持一點距離,老師對學術研究與其他社會參與之間,角色關係的想像是什麼?
廖:我沒有感受學術與實務那麼大的衝突,除非我迷失自己。對我來說學術研究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礎,我必須在這些主題上瞭解更深入,才能提供我去從事人權運動與政府諮詢的基礎,使我同時可以扮演好三種角色。除非我變成蛋頭學者,不然這對我來說沒有衝突,因為主軸、角色、目標都是一致,不管任務是要做國家行動計畫、人權條約內國法化等等。我這21年來投入推動國家人權委員會,如果學術上沒有增長,我是無法有所貢獻的。
不過角色雖然沒有衝突,時間上是有衝突的,另外是實務參與也會造成學術發展的壓力,因為還是必須面對升等。我升等其實是非常坎坷,我把學術研究全部投注在這邊,就比較不符合純學術的TSSCI或SSCI的出版要求,我也不會把自己的研究定位成完全學術的研究,我的讀者也不是只有學術社群。
我定位我的研究是有策略的學術研究,我希望臺灣怎麼去和國際人權接軌,所有的寫作都是從這個角度,包括要選什麼題目,要怎麼思考,不會單純只從學術中人的思考去做。可是這樣的研究還是學術研究,我很清楚學術文章與政策諮詢的寫作不同,只是寫作學術文章的同時,不會只想像這是完全學術的題目,會有策略的定位。例如我針對國家人權機構寫了兩本學術的書。第一本書的策略是去看個別國家的實踐,像蟲一樣鑽得深入;另外一本書,我就像鳥一樣,從空中鳥瞰整體的圖像是什麼,這是我想過以二個交錯的角度思考。交錯以後我就知道個別國家的狀況與大幅度的情況,這些在作人權諮詢時,成為重要素材。因為要設立國家人權機構,一定要瞭解背景資料,所以我就做這樣的整合。
問:那當老師拿著研究成果去建議行政機關該怎麼做的時候,會不會遇到行政機關覺得這就是書生之見、很離地?
廖:常常啊,可是至少這二十年來的經驗告訴我,情況是有改善。我常開玩笑說這叫火車進化史,一開始叫狗吠火車,或者根本連火車都沒有,慢慢開始有台鐵的慢車,可以上車了但很慢,然後有高鐵。實際上真的有改善,但永恆不變的是,我永遠不是政府的人。建議跟最後的實踐一定會有落差,只是落差多還少,但我知道我不是政府的人,我要的是整個臺灣國家社會的系統慢慢改良,即使一開始零分也沒關係,只要變20分、30分、50分、80分,我要的是它不停地往前走、不斷地進步,但這你不覺得這也是學者要做的事情嗎?我一直自我界定是要參與改良社會的學者,透過學術研究、民間運動、政府諮詢,我的目標就是要改良臺灣社會。
問:老師很早就立志要走人權工作的路線,但那時候臺灣都沒有這樣的環境,所以我好奇有什麼因素影響了老師立定人權工作的志向,一路堅持?
廖:我成長的背景是臺灣民主運動。我1965年出生,大學畢業那年剛好臺灣解嚴1987年,剛好是臺灣民主化運動的過程。臺灣的民主運動、民主啟蒙的環境對我影響很大。我一直在想,臺灣民主化以後應該是要有人權的建設,以前做民主運動是要勇氣,要不怕死、敢走上街頭,但接著就要有實質的建設,這是質的問題,我因此偏向於投入人權的法律。
我每十年,20歲、30歲、40歲、50歲,都會有自我的大辯論。我大概是大二時、20歲,算是給自己的成年禮,那時候念法律的人都會想以後自己是不是要當法官、當檢察官,是不是要當律師,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我要當個學者,所以我從不質疑我要當學者,我質疑的是我要念憲法還是國際公法。
現在回想起來很好笑,才大二很多法律課程根本都還沒念過,就在擔憂這個事情。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要投入憲法跟國際公法,我對廣義的公法有興趣,其他的商法完全沒有興趣。20歲的時候主要是想念憲法,那時候還覺得自己抓摸不到國際法,這是時代背景,我們社會被國際封鎖。
後來我進入臺北大學念公法組,遇到蘇義雄老師,他是留學法國史特拉斯堡,也就是歐洲人權法院的所在地。他講授歐洲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談到國際人權訴訟,那時候我就覺得說:「這不就是我想要的嗎?」這太好了,我要的就是國際人權法,因為它結合了國際法跟憲法,重新燃起我對國際法的興趣,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一路都寫歐洲人權公約,後來才慢慢擴展到聯合國。國際人權訴訟非常吸引我,我因此決定到英國繼續去念歐洲人權公約,寫公約第10條的表意自由,我在牛津的指導老師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個臺灣人要念這個?因為當時英國都還沒有把歐洲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是連當地都不見得很熟悉的年代,有臺灣人要來念他覺得很有趣啊。他本來還建議我寫比較法,至少有些臺灣的內容,但我拒絕,我要寫純歐洲人權公約的論文。

問:老師對下一代人權工作者有什麼鼓勵與期許?
廖:我其實不太敢亂建議。人生是投注跟賭博。選擇每一個領域都有好跟不好、樂觀不樂觀。先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是不是真的準備好投入,不要因為風潮或一時感受,真的想過這是我真正想要投入的領域,還有以後的出路。雖然投入人權領域是有可能成為人權律師,不過臺灣沒有純粹的人權律師,當法官、檢察官不可能說我是人權法官、人權檢察官。
如果要比較完整地做人權法的話,就是在學術界。但學術界相對而言必須承擔寂寞,雖然我們都覺得人權很重要,可是人權法律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可能永遠都不會是法律系的主流。想清楚,才會有主觀的動力,這比其他都重要。這個主觀動力是對價值的衡量,認為自己投入這個領域是有價值的。
問:那老師未來十年想做什麼呢?
廖:我有三個方向,第一是商業與人權,對我自己是比較跳出舒適圈。本來我對商事法完全排斥,但現在要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就會碰到。今年三月以前我在擔任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回來以後我就想這是一個契機,商業與人權可以作為一個方向。
第二個是再把憲法跟國際人權法交結在一起。有些國家在憲法裡會直接規定國際人權條約的憲法地位,這個臺灣沒有。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些國家會想要把國際人權公約放到憲法的位置上,放了以後對於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會有什麼影響,實質上會有什麼刺激,權利的概念可以也應該結合憲法跟人權法。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未來我們臺灣如果要有進一步的憲政改革的話,我們就要先有學術研究,你看得出來我是這樣一個脈絡,這是我策略性學術研究的思考,未來如果有修憲、制憲機會,我就可以提供這些論述。
第三個是我覺得臺灣缺乏國際人權條約國內法化的基礎建設,更進一步的基礎建設是回到個案,聯合國人權公約裡有個人申訴的個案,我希望把各國違反公約的個案全部彙整起來。一方面滿足我自己好奇心,我想要解開一個疑惑,就是國家為何會違反國際人權條約?在什麼樣的狀態下,國家會違反?另一方面,這也是策略性研究的體現,因為我們法院碰到的問題是,它不知道國際人權條約要怎麼用,所以我就提供活生生的案子,讓法院以後碰到類似案件可以參考,這就提供了社會改良的基礎。我想如果可以在未來十年內,把這三個任務完成,我應該算是盡力、無愧了。
歡迎加入法律所官方臉書,以便快速獲得更多相關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iiastw(另開新視窗)
